徐洪,1936年在澳門出生,從爺爺那輩起就是上架行的人,爺爺就葬在上架行的墓地。他六歲時父親去世,他的三個兄弟在澳門“風潮時期”餓死,只剩他一個孩子。1951年鏡平小學畢業後,就學師做木藝四年。1955年出師後一直在澳門鴻昌隆傢俬公司做木工,也曾做過澳娛的裝潢工程。1974年以後成立了自己的公司,做些判頭的工作,至今仍然從事相關行業。

圖1 徐洪,澳門上架木藝工會提供。
我家三代入工會
我叫徐洪,1936年出生。我爺爺這一輩、我爸爸再到我們,三代人都在澳門生活。據我所知,有三代人了,因為我爺爺也在上架行。當年上架行在珠海有一塊墓地,我爺爺就是葬在那兒,所以我們才知道爺爺是好早就入上架行。我爸爸是做泥水工的,加入了泥水工會。我爺爺和爸爸早在民國初期,已加入上架行會,那時清政府是反對籌辦工會的。
我沒有見過我爺爺,但是我到過爺爺的墳,很遠的,在珠海白蓮洞、吉大附近,那塊地很漂亮的。當澳門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“風潮時期”1之後(即1945年後),有很多人都到處找尋自己的祖宗山墳,以前日本侵略中國時,有很多山墳都不見了,我太公的石碑都遺失了,在垃甲山(垃圾山)即是在近拱北上面,那時日本人要用石碑來建堡壘,有很多石碑都因此找不到了,慶幸我們找回爺爺的墳,太公的墳就找不到。1945年日本投降,我們就找尋祖宗的山墳,找回了爺爺的墳。我們工會有一塊墓地,是屬於上架行的。
在50至60年代期間,政府就收回該地,將那裡的墳全都遷到合羅山,所以爺爺和爸爸的墳都遷到合羅山了。
那時的墓地有很多都是同鄉會的,有姓陳,有姓李,在拱北上面有很多墓地,亦有林西河堂等,很多會都有地的。我爸爸的墓地就在灣仔那邊,西樵同鄉會的,是傅老榕買了塊地供同鄉會使用,他是西樵人,開賭,大把錢啦,在灣仔買了幅地。清明節,就會邀請全部鄉親回鄉祭祖。那時全部用“花美大渡”(有漂亮裝飾的大船),舉辦的活動挺好的。
現在都沒有了,現在全部墳都遷到合羅山,合羅山之後再轉變,全部搬到澳門。時代變遷了,無論在用地方面、費用方面,令我們都全部搬回澳門了。
風潮時期艱難度日
三年零八個月的“風潮”時,我五六歲,本來生活是不錯的,因為我爸爸是做泥水判頭,以前新馬路著名的英記餅家、顯記餅家的泥水工程、打灶頭等,都是我爸爸負責做的,就是做裝修同打灶,但主要是打灶頭。之前打灶頭的要求是能“慳柴火”,最緊要是“慳”,以前要“平、靚、好”,無論做甚麼都好,最重要是“慳料”,那時生活環境都比較好。
後來三年零八個月,環境變遷,在我六歲時,爸爸去世,我們的生活很艱苦很慘,無糧食。因為當香港淪陷,就無米運輸到澳門。以前很多物資都要靠香港運輸的,大多數的人都是因缺糧而餓死,包括我自己的一些兄弟都是因為這樣而死的。
本來我有三四個兄弟,現在就只剩下我一個了,其他都是在那時候餓死的。我是第四個,是幼子,靠媽媽帶大我的。我媽媽是做神香的,即是拜神用的神香。

圖3 澳門中式廟宇中常見塔香,澳門上架木藝工會提供。
我在深巷仔出生,即是清平直街後面有條叫深巷仔,後期就搬上三巴門,即是白鴿巢行落少少。都是住木屋,那種兩層高的木屋,主要是租住。早期在深巷仔就全個平面地下自家住,後期生活困難,在三巴門就住兩層高的平房,一層五伙人住,一個廳就兩伙人,走廊住一伙,兩間房就住兩伙,就是這樣子,那時候生活是很困難。
當時我們主要是吃菜頭菜尾,吃粥水,後期連粥水也沒得吃,那時生活真的很困難。
在澳門,我每日看見有人在街上撿屍骸,日日我都見到,是在我七八歲,第三年,在街上,死的人最多。該如何形容呢?那時就如現在的垃圾車在垃圾站收垃圾,就是這樣撿屍的。屍體就堆放在街上,堆滿了,就每天早上來撿屍。不是用車撿,是用木頭車推着撿。
那時我聽人說,屍體都是丟放在氹仔墳場的對面,即是氹仔北安,就這樣用木頭車推去青洲上船,再送到氹仔北安,淨用泥土埋屍,其餘甚麼也沒有。
這就是三年零八個月的環境,非常艱苦的。差不多每個家庭都有人是餓死的,有些年青力壯,就像我舅父,他有能力工作,但都無工作可以做,最後都是餓死。我大哥也是這樣,到後期餓到水都無辦法飲,用粥水餵他,他都吃不下,連吞的力氣也沒有,想救都不能救了。
到處掙扎求存
我們要生存,就要到處掙扎求存,去打工。我八歲大,就到現在的望廈體育館,以前那裡是海,現在的俾利喇街的公屋,以前是兵營,是山來的,我們就在那裡掘山泥石,用來填現在望廈體育館那塊地。那時我只有幾歲大,有些較年長的好心人就向我說:“細佬,你撿一塊咁大的就得啦!跟住我行啦!”這樣做一朝,就有一碗“Sopa”(葡文:湯,粥),即是將一些馬鈴薯、豆類、蕃茄等煮成粥。
我媽媽就在新口岸,聖心學校的位置,以前那裡是山來的,她就擔泥到總統酒店對面的位置,那裡有一條長命橋,就在那個位置填海,以前那裡是海來的,即是松山腳位置是海來的,現在是聖心學校,一直出去就是利澳酒店等,那邊的地方都是填海填出來的,所以要用人來擔泥。
媽媽由早上擔泥至夜晚,大約可以擔到十擔泥,因為路程較遠,擔一擔泥就有一個籌,十擔泥就可以換到一碗粥,那只夠她吃,僅足夠一人吃,我們沒飯吃。後期就到同善堂,在台山口派發粥水,有很多人去的,那時候顧不了那麼多,哪裡有得吃就到哪裡去了,這樣才得以生存下去。
那時是葡國政府填海的。他是救濟,不過在救濟過程中,他不讓你不勞而獲就有飯吃。而同善堂是需要憑證才能取粥的,那時要有社會人士認為你很窮才能拿到那張證,不是隨便派給人的。
感恩何賢
在1945年,我九歲,正正是日本投降的時候,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,到11、12月,我就到蓮溪廟報讀寒假班,下學期的課程,在蓮溪廟旁邊的位置,以前是平民學校的分校,現在那學校還在。
請了半年之後,到1946年就去到竹林寺對面那裡,即現在百佳超級市場的位置,那裡是平民小學,由何賢先生當校長,全免學費的。
我們澳門人都會記得何賢,因為沒有他辦免費學校,我們就沒有書讀了。
1949年,我就在俾利喇街至美副將轉角位置的鏡湖平民聯合小學讀書,合稱為鏡平小學,當時也是由何賢當校長,直至1951年,我就小學畢業。之後就投入社會,去當學徒。
拜師學木藝
我小學畢業就去學木藝,跟林姓師傅學師,他是新會人。他已經走了很久了。那時在石牆街魚鯉圍學師,做了四年學徒。
當學徒是一定要做家務事的,包括擔水、煮飯、洗衣服、整理師傅的用具等。那時我要住在師傅的家,因為你不住師傅家,是沒法做完那些功夫的。早上最遲六點半要起床,做到晚上11點,中午食完飯可休息一會兒,之後就沒有休息時間。每天晚上都要開夜工,逢初二、十六我們稱“做伢”,就各休息一晚,一個月有兩晚休息。過年都有三日休息。
我學師四年,1955年出師,到外面自己做木工,做傢俬,都是在澳門工作,沒有到香港工作。我在鴻昌隆傢俬,位於花王堂街,一般俗稱“長樓”,即大三巴那兒,我在那裡工作了三年。現在那位置已全部重建,店舖已不在了。
之後我就四處做散工。通常我們做傢俬都是逐件計工資的,例如做一個櫃要多少錢,做一張床要多少錢,做一張椅要多少錢,當時我在鴻昌隆做最大的工程就是冠男茶樓,位於十月初五街。現在冠男茶樓都已結業,那兒的枱和椅子、卡位等全都是我們做的。
我們都是按“件頭”計,即依每一個製成品多少錢來計算工資的,稱為“計件工資”,做一個櫃,一張床,一張木椅,要多少錢,依早上八點至晚上十點。
無論我們或是師傅,平均每人大約每天四塊五毛錢。各有一個小時食午餐和晚餐,但大多數都是少於一小時的。
我們當時大部分人都是單身,生活環境比較好。如果是有家庭,有幾個人需要照顧的話,是很辛苦的。我的一個拍檔跟我說:“我回家吃飯,不是坐着吃飯,吃完就休息,我是要口中那口飯還未吞就要起程開工,邊吃邊走。”
當時的環境就是這樣。但亦要視乎你的工作能力、效率。工作快,就可賺多點錢,最厲害的那個人可以賺到一日五塊錢,有些人就賺四塊錢,我們就剛好是中位數,四塊五毛錢。
從早上八點至晚上十點,要14個鐘頭啊。即是“計件工”之中,你只能賺這麼多錢,老闆們對工資都計對計盡,不給你多亦不給你少。
每天都要工作至晚上十點,不工作這麼長的時間,你簡直連三塊錢也賺不到,如果你有家庭,真的就要借錢度日、借貸度日。
要說起有什麼保險?甚麼都沒有,沒有任何保障。假若發生甚麼事,有甚麼困難,就要靠自己的親戚朋友、工友們湊錢來幫你。有些人有病,不能工作,就靠工友們大家互相幫助、接濟。
工友間相互合作
我1968年結婚。在鴻昌隆之後我一直做散工,若社會上有些較大的工程,就會找幾位拍檔合作,接下工程一起做。
新公司,即現今的澳博,以前稱為澳娛,當初接手舊公司(我們稱為中央公司的,老闆是傅老榕),在1962年,澳娛投得賭牌,我們一班行家,包括羅泉在內,共二三十人,接下澳娛的臨時裝修工程,須於11日內完工,要趕緊開張。
那時澳門有七個地方被租了開賭場,我們就從早到晚,不停趕工,我們都慣了長時間工作,就日夜做。主要是做賭枱、天花、牆身等。我們11天完工,趕起七個賭場,一班人完工就各自散。
有時我們都會做學校的書枱和椅子,或政府有工程,我們都會做的。
雖然是做散工,但工友間都會互相合作,誰有工作,都會介紹給大家一起做,很多工作都是這樣判給的。
我現在有三個子女,三個孫。他們都不繼承我的行業,我們上一代的行業都已沒有人接手再做了。慶幸子女們都讀到書,現在有幾個子女都是教師,沒做我這行業,全都做文職。我們三代都是工人,我爺爺是工人,我爸爸是工人,我也是工人,到我的下一代就全變成文化人。
自己開公司
在70年代,我們一班工友接了葡京酒店的裝修工程,足足做了四年,主要做酒店內的裝修和傢俬,葡京酒店內的酒樓餐廳的裝修和設備、枱子、椅子等,我們由1970年開始做,做到1974年。
之後我自己成立一間公司,做一些類似我師傅的“山寨”式工程,自己接到工程就找一些工友一起做,由我負責聘請一些人做散工。那時我做的工程種類較多,包括水電、冷氣、油漆,所有屬於裝修範圍內的工作,我都承包,然後再分判給其他人做,我就充當判頭的角色。判頭是一個工程內,他只佔一部份,我做的是總承判,即將整個工程總攬之後,再分判給其他人。這不是生意上的老闆,是工程上的老闆,要自己動手的,木工就自己做,水電等工作就分判給別人做,這是一種合作的形式。
這樣的收入比打工理想,自己有一份人工,再多少加一點其他利潤,生活上算是不成問題了。
捨不得這個興趣
在80年代之前,我也有教過一些學徒,有些讀不成書,有些讀到書,我曾教過一位學徒,是在培正讀到中五畢業的,我就跟他說:“你係中五畢業生,你學我呢行好似有點浪費。”但他喜好做木工,結果他表現都不錯。年輕人學一些手藝是有好處的,他現在是導師,我眾學徒中前景最好是這位了。
可能是因社會環境變遷,有些學徒出到社會找不到工作,就轉行做警察。現在我還不算是完全退休,接到一些工程,我都交給我的“下手”做,幫我工作的時間比較長,知道怎樣的功夫才能交貨,標準在哪裡,我就交給這些人做。
木工是我的興趣所在,我就是捨不得這個興趣。但現在都逐步退下來,自己已經不會動手做,都交給別人做。
“行街”三個月
“一二.三事件”那段時間,澳門好困難,我聽我的前輩說,從未看見市面一片蕭條,沒有工作做。1967年那時候,我剛好沒工作,每天往街上跑,足足三個月。幸好自己出身於困難環境,平時不會隨便亂花一分錢,儲蓄起來,那時候就有錢花,有些人沒錢就借錢度日。
我足足“行街”三個月。這可說有好有不好,我就在這三個月中結識了女朋友,之後1968年結婚,本是壞事卻變成了好事,不然連拍拖談戀愛的時間都沒有,日日都要工作,所以我把它看成是好事,我多了自己的私人時間。
“一二.三事件”對澳門市民有很大的影響,整個澳門市面全都靜下來,以前澳門的經濟是靠香港的旅客來帶動消費,澳門其他本身的經濟發展是很慢的,以前澳門少工業,後期才發展旅遊業。
發展旅遊業之後,澳門的社會環境變好。後來葡京酒店開業,澳門的經濟發展隨之興旺。
入工會
我1955年加入工會。那時會員應該有四百多人,領導人是梁培、馮培、伍培,合稱“三培”。
初期我是聯絡組的組長,我在三巴門曾經派聯絡通告,例如有師傅誕等活動、勞資糾紛、提工資等資料,都會派通告給工友。基本上我整個三巴門中有24至25戶人家是由我負責聯繫、派通告的。聯絡組的工作我做了約十年。
後來工會成立福利會,主要處理勞資糾紛、辦保險。那時候愛都酒店加建樓層,有個女工意外失足死亡,該建築商不願賠償,結果促使工會成立福利會,主要負責辦保險等事宜,向建築商徵收一天四毛錢,以作為每一位工人工作一天的保險金,不是從工人的工資拿四毛錢。
愛都酒店的事大約是1963、1964年,那時娛樂公司開業不久,要加建一層。我們沒有參與加建樓層,只在地下做裝修。在此單工程中,那位女工在加樓的時候,不斷退後,由於沒有圍欄,失足下墮至天井。
這是我親眼所見,很可憐,一屍兩命。
後期建築商想推卸責任,我們為表支持,開始鬥爭,結果都爭取到,建築商要賠償數千元,那時候一個工人的工資約為11元。之後就成立工人福利會。直至現今福利會仍存在,只是沒有再收四毛錢,現在全部有保險。
我愛合唱團
我一直都有參加工會的活動,亦有參加青年團體的工作,主要著重於青年團體的工作。我是“語運合唱團”的成員,位於十月初五街106號三樓,它是“國語運動協進會”屬下的一個合唱團,簡稱“語運合唱團”。所以那時候我們也有學過一些普通話。
現在的青協,由三個青年團體改名而來,“語運”、“群青”、“青聯”。
合唱團有百多人,主要唱革命歌曲,我們每年的“七.一七”是紀念聶耳先生的,例如《黃河大合唱》,我們以前都有唱過,有四部合唱。
以前我們多舉辦的是籌款活動,由數個青年團體,包括學聯(學生聯合會)。以前有很多籌款活動的,例如勞校籌款、鏡湖醫院籌款,很多的社團籌款活動我們都有參與。

圖8 60年代全澳同胞慶祝國慶經費捐冊,澳門上架木藝工會提供。
我在1955年參加青年團體工作。工會和青年的工作,我較為著重於青年的工作。那時我年輕,20歲左右,正式青年,亦可以學習一些其他活動,例如音樂、普通話、攝影、縫紉、裁剪等。
我們的活動場地都是用會費租的,月費是五毛錢一個月,由大家來支付,房租是70塊,每個月的支出是120塊。
早年的工會煮食
由我做學徒的時候,師傅已經叫我去參加師傅誕的聚餐。那時師傅誕有兩餐,(農曆)六月十三日一餐,年尾十二月尾誕有一餐,共兩餐,就算師傅不出席,我們都會自己出席的。
我做學徒時,梁培、馮培有來過我們工作的地方訪問過,他們說“你們做學徒都可以入會的。”動員我們入會。
後來我到出來工作才入會,但未入會前我都有參加工會的活動,例如一年兩次聚餐。
那時的聚餐都是在工會裡面,飯菜都是找人來煮的,八個人一圍枱,一張四方枱,菜式有粉絲煮蝦米,拜完師傅後,我們就有燒豬肉食,要食魚就一定要食鯇魚。那時在正門口煮兩大桶飯,有很多街坊排隊取飯的。以前的人較迷信,相信食完師傅飯的人會乖、快高長大。除了有飯,還有餸,都是一些瓜菜類、少肉、粉絲蝦米等普通的餸,沒有計算要派多少份飯,就是一桶那麼大,派完就沒有了。多數都是附近街坊來取飯,直到沙欄仔那邊都有人來,以前澳門的人口不多。

圖9 師傅誕正誕,工會行友圍聚八仙枱聚餐。澳門上架木藝工會提供。
到酒家食飯的時期,已經開始沒有派飯了,大約是在工會辦學校之後,因為沒有地方煮。1950、1951年的時候還有煮。後來工會變成勞校的分教處,後期就全部人都入了勞校。
1952年興建勞校,位於永樂對面,我們親眼見到起勞校的。初期第一天,我就跟一個泥水師傅到蓮溪廟,工作了數月就沒有做了,結果我就入了木工這行。
上任會長
我參加青協的活動,若以彼此會員間的關係,一直到今時今日都在的,但以負責的工作來說,自1968年結婚後就開始減少了。我在社團工作了數年,以前是合唱團的團長,後來是主席,正所謂“曲不離口,工不離手”,現在我少練習了。
木藝工會的會長我剛剛上任,我是掛名的,主要是靠他們理事長幫忙工作,我只是在整個架構上掛個名而已。

圖11 “慶五一”活動,徐洪(左)向工友頒發獎項。澳門上架木藝工會提供。
工會舊事
在澳門搭建牌樓,我們積極參與。之前我們有建過南光的牌樓,以前雷洪是做南光的,南光的牌樓年年都是我們搭建的,位於下環街南光舊貨倉。大會的牌樓我們較少搭建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時期封了木藝工會的魯班師傅神像,我只是知道這件事。大約是1967年,“文化大革命”剛開始就封了,賣出工會的香爐鼎,聽說賣出時為數百元,後來有個香港人拿去美國拍賣,叫價萬元以上,那是古物來的。很久前遺留下來的,是清朝咸豐年的時候,大約距今有170年。
說到要找工作就到上架行會館,我曾經有回去過,以前在澳門,我們的行家、判頭,那時林渠、陳滿、黃錦全、張冠福他們四個人,分屬澳門不同的建築公司,大家合作,我這裡請人,就到你那裡找人來工作,他們四個人基本上有工作做的。但我們做散工的,若想找工作,就到工會找他們四個介紹。他們四個都是負責人,是理監事來的,以前有些是做副主席、財政。這是60年代的事了。
工會有章程,我們現在三年一次改選。我是今年這一屆,剛剛當選的會長。現在我們會有900多位會員,以澳門來說,我們會館算規模是比較大的,因為我們是工聯創會的會員之一。
早年的會館
上架行會館是由我們這行業的人士成立的,以前有慈善機構永壽堂、廣義堂,永壽堂每年有一個會慶活動,按照俗例,五月初八龍母誕會舉行集會,因為以前清朝時是禁止集會的,不批准工會集會,以防造反,我們就只可藉着廟宇、神誕來舉行集會,叫永壽堂。
永壽堂一樣是有會員證的,我仍保留着該會的會員證,這樣東西我保存得最好的。入會的時候會有一本證給你的,你入會要一次性交會費,之後每年都有免費聚餐。後期由於要辦醫療福利,但工會無錢,每人只有收很少的會費嘛,所以吃完一餐以後每人要支付五毛錢,以作為醫藥補助。
以前我們工人到工人醫療所,只需支付數元醫藥費,但工友們仍可享有幾毛錢的醫療補助。每個會員參加永壽堂的,以前就免費,後期就每人支付五毛錢作醫療福利補助。
反對國民黨勢力的鬥爭
1956年期間鬥爭最激烈,最主要在搞國慶活動時,除了要建牌樓,還要守夜,我都有試過守夜守牌樓,晚上要輪更。另外我在自己的社團,晚上也要輪更守夜,一人守兩小時,因為怕晚上有人破壞、搗亂,那時澳門形勢很緊張。所有要扯五星國旗的社團機構,晚上都要有人守夜,因為只要國民黨搗亂到一個社團地方,他們就會大肆宣傳,所以要防止他們搗亂任何一間社團。後期他們在街上扯國民黨旗,趁無人發現的時候在街上丟傳單,因為他不敢到社團的地方鬧事,就唯有這樣做。你有準備就好,你沒有做準備,別人就會乘機破壞。以前我們每個人都很緊張的,10月1日的時候我們都穿大褸,那時天氣很冷,又是年輕人,半夜要起床很辛苦的。那時候也很後生啊,20多歲。
對國民黨勢力,我們沒有醜化他們。以前他們多找一些黑社會的人,例如14K、水房等黑社會都是他們的人,他們的人多屬於流氓,他們很少是做正行正業的人。正行正業的人多數是我們的人。
事關行業傳承
雖然我現在到這個年齡,一方面要打理自己的生意,另一方面要當900多個會員的會長,但是我盡自己的能力,做到多少就做多少,支持會務和集體的活動,爭取大家工人的利益。
現在我們的會員,大部分都是大年紀的,年輕人佔很少。我們這個是行業的工會,如果這個行業沒有年輕人願意做,就肯定沒有年輕人的會員。所以直到現在,我們木藝工會都了解到這行業逐漸式微的情況,同時為了能將魯班先師的木工藝傳承給世人知道,即使這行業日漸式微,但我們亦希望可以傳承給後人知道,因此現在我們利用上架木藝工會會館的一個地方,籌備一個名為“魯班木工藝”的陳列館,將我們所使用的工具,通過介紹這些工具的使用過程,令更多人認識木工藝,現在正在籌備當中。
現在的年輕人,怕辛苦,收入不穩定,真的要做這一行,無醫療,無福利,無退休,幾樣都沒有的。就像我們,雖然回歸以後,很多福利也沒有享受到。現在主要靠社會保障基金,即每一個月供多少錢,然後到65歲的時候可以拿到多少錢,其他甚麼退休金,我們都沒有的。
我們靠的都是自己的積蓄,有精神、有能力時多做點工作,把工資儲蓄起來。因為我們這代人初初出到社會,知道生活困難,就比較珍惜錢,不會輕易亂花錢,全都是辛辛苦苦、有血有汗的一分一分錢儲蓄起來的。我們學師,做學徒的時候,一個月才一塊錢作工資。你替師傅工作,他就包食宿,那時理髮要五毛錢,買一個麵包要一毛錢,一日就要食兩個麵包,早上八點食一個麵包,直到下午四點再食一個麵包,一日食兩個麵包,一個月才一塊錢工資,錢就必然是不夠用的,我們就問媽媽拿錢,這個環境足足生活了四年。那時候我媽媽是做神香,做了幾十年,做到80歲才沒有做。
為媽媽爭取一分錢
講到我為什麼會加入工會呢?主要是有兩個原因,一方面是工會的負責人來動員,另一方面我跟媽媽到工會鬥爭,爭取解決勞資糾紛。在50年代的時候,1,000枝神香就“七點子”,即係“七分錢”,不足一毛錢,那時我們要求廠商加到一毛錢1,000枝香,後來我們爭取到八分錢、九分錢,一分錢、一分錢逐漸增加嘍。那時要大家開會,爭取其他工會的支持,這才可以鬥爭成功的。要鬥爭得好激烈才能爭取到一毛錢。那時我跟媽媽一起去開會,為了那一毛錢,已經鬥爭得好激烈了。要爭取到自己的利益,就要參加工會,所以我加入了工會。
親眼見證濠江小學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
記得大約是1950年,在鏡湖馬路的濠江小學,當時國民黨的人來搗亂,不給升起五星紅旗,國民黨的人扯着國民黨旗來搗亂,一大班人彼此維護自己支持的黨派,就開始鬥爭,你推我撞。但是很快就解決問題了,因為擁護五星紅旗的人越來越多,人多對人少,國民黨的人少,所以就離開了,停止搗亂。當時我雖然年紀小,但我們都很喜歡去看這些的。第二枝紅旗我就沒親眼看到,但我聽說是在十月初五街的志光百貨公司,老闆為陳植生,他是愛國商人,在澳門有很多愛國商人都很熱心的。
注釋:
1. 1941年12月,日本佔領香港,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,總共三年零八個月的時間,港澳人習慣稱之為“風潮時期”。
更新日期:2020/09/15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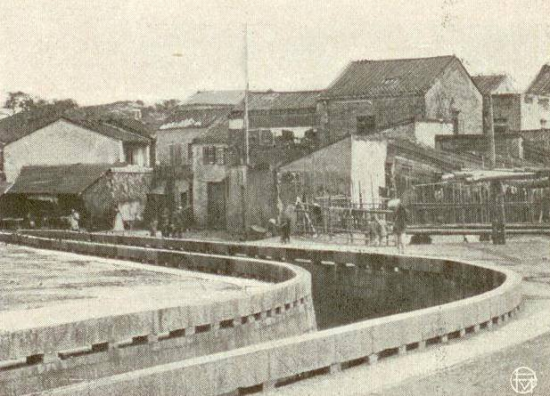
留言
留言( 0 人參與, 0 條留言):期待您提供史料和真實故事,共同填補歷史空白!(150字以內)